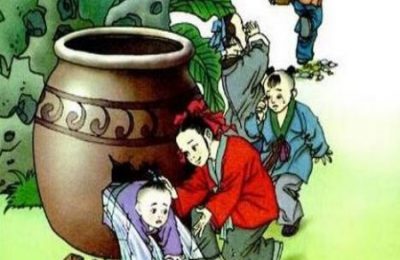校园地处偏僻,距离最近的小镇也有四五里地。改革开放之前,一切物资都限量供应,凭票购买。国营商店大多开在小镇上,买一块豆腐、称一颗白菜都得去付食店排队,更别说肉和鸡蛋,那队伍如长龙,会从店里一直蜿蜒到大街上。
大哥后来会经常提起当时买肉的情景。母亲之前叮嘱他,肉一定要带些肥膘的,回来可以提炼猪油,一日三餐里会多些油水了。大哥快排到柜台前时,先要向里张望一翻,如果正赶上瘦肉,他便掉转头,从队尾重新排起,几次三翻,直到买上肥肉才罢休。
排队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常态,于是同院的父亲们在买东西之前会准备一本书,边排队边看书两不耽误,也成了街头一景。这边母亲们也动起了心思,既然买东西这么难,干脆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于是在门前的空地上开辟出一块块菜畦,种些时令蔬菜,既解决了少菜吃的难题,又美化了环境。有时进得小院,菜畦里绿油油的青菜,肥嫩的豆荚,藤架上的丝瓜、黄瓜,满眼青碧,绿意盈怀。这一场景在许多年后还会时常出现在我梦里。梦中见到那一块块油绿,依然满心欢喜,这碧绿的色彩给我童年贫脊而单调的生活带来多少希望啊!有了这一片片的绿为生命打底,即使后来的人生中面对再大的挫折,我也从不绝望。
当然在菜畦边上还要种些花草的。身为知识分子的母亲们不会拘囿于一粥一饭,总是要有些精神追求的。母亲种了几株萱草,俗称“黄花菜”,这种菜花蕾时就要摘下来晒干,可我太想看它开花的样子了,于是央求母亲为我留了几朵,放学回家,远远便能看到几张金灿灿的笑脸,让人心花怒放。不过母亲在它们快开败时还是悄悄摘下来,用开水焯了焯,做菜用了。后来,我才知道,这种花还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,叫“忘忧草”。